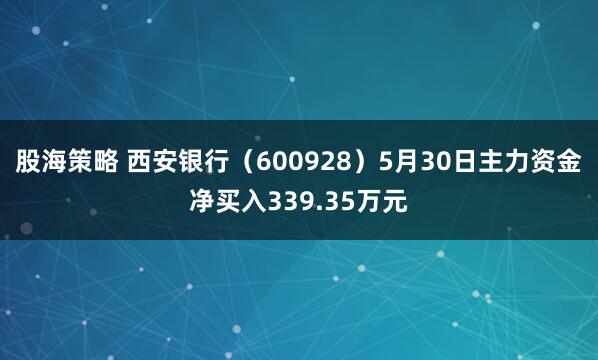我生命中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父亲暴怒时的样子。那些画面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脑海里,这么多年过去了衡牛所,依然清晰得可怕。记得那时候,只要父亲脸色一变,我的心跳就会瞬间加速,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咒一样动弹不得。他的怒吼声像炸雷一样在耳边炸开,有时候甚至不用喊全名,光是听到我名字第一个字声调变了,我就知道暴风雨要来了。
我永远记得那种魂飞魄散的感觉。小小的身体完全僵住了,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最羞耻的是,明明已经吓得快要尿裤子了,却连挪动一步去厕所的勇气都没有。有几次我就那样直挺挺地站着,直到温热的尿液顺着大腿流下来,在地板上积成一小滩。奶奶发现后赶紧来拉我,我就这么机械地跟着她走,身后还拖着一条湿漉漉的痕迹。那种耻辱感和恐惧感混合在一起,成了我童年最深的创伤。
说来也真是讽刺,成年后的我竟然鬼使神差地选择了一位和父亲脾气如出一辙的研究生导师。这位东北籍的女导师在业内是出了名的"暴脾气"衡牛所,学生们私底下都叫她"手术台母老虎"。我第一次见到她发火时,整个人都恍惚了——那涨红的脸、暴起的青筋、喷溅的唾沫星子,活脱脱就是女版的我爸。更神奇的是,我们课题组十几个学生里,我是唯一一个没被导师骂全乎的。那次她刚训斥到一半,突然发现我脸色惨白、双腿发抖的样子,竟然破天荒地停住了。后来我听同学说,当时我的表情就像只受惊过度的小鹿,连"母老虎"都不忍心继续吼下去了。
展开剩余66%这种对暴怒的恐惧,让我发展出了一套近乎完美的"生存策略"。在读研期间,我养成了近乎偏执的完美主义习惯:实验数据要反复核对五遍才敢上交,论文初稿永远提前一个月完成,发现任何小错误都要立即主动认错。我还发明了个"危机预警系统":预判所有可能出错的地方,提前准备好三套补救方案,确保在导师发现前就主动报告。最夸张的一次,我为了修改一个微不足道的数据偏差,在实验室熬了整整四个通宵。同门都说我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但我知道,这不过是童年练就的"保命本能"罢了。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五味杂陈。父亲的暴怒虽然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却也阴差阳错地造就了我的某些"优势":超强的抗压能力、敏锐的危机意识、极致的完美主义倾向。导师经常当着全组的面夸我:"你们都要向XX学习!她是我带过的最让人省心的学生。"可她不知道,这份"省心"背后,藏着多少童年时尿裤子的恐惧记忆。毕业时导师拉着我的手说:"你爸妈真不了解他们的女儿有多优秀,让你这样回到家乡小城市真是浪费人才!"她哪会明白,正是这个"不了解"我的父亲衡牛所,用他特殊的方式"培养"出了现在的优秀的我。
来花径后,我终于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暴怒,看到了爸爸小婴儿的无能和无奈,同时,也正是这种"有毒"的教养方式,让我鬼使神差地适应了严苛的学术环境。就像长期服用微量毒物的人会产生抗药性,我对"暴怒型权威"也产生了某种特殊的免疫力。现在的我,偶尔我还会梦见那个吓呆的小女孩,但我终于可以比较平静地看待这段经历:承认创伤的存在,接纳它带来的双重影响,学会与过去的自己和解。
这段特别的成长经历,就像一块有瑕疵的玉石——那些裂痕反而造就了独特的光泽。父亲的暴怒给了我伤痕,也给了我力量,这大概就是最真实的"非爱之爱"吧。我终于明白,那些让我发抖的暴风雨,最后都变成了浇灌人生的养分。而那个曾经被吓得尿裤子的小女孩,如今已经长成了能够从容面对任何风暴的女人。
编者评语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童年面对父亲暴怒时的生理性恐惧——那刻入骨髓的颤抖、窒息般的僵直、乃至失禁的羞耻——赤裸裸地呈现于我们面前。那些画面,如同被岁月也无法磨灭的烙印,成为生命最初的、也是最沉重的底色。
然而,故事的走向并非简单的控诉。命运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份深植于童年的恐惧衡牛所,竟阴差阳错地锻造了作者独特的生存盔甲。最终,她理解了父辈的局限与挣扎(“爸爸小婴儿的无能”),更重要的,是与那个被恐惧定格的小女孩达成了和解。
发布于:北京市高忆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