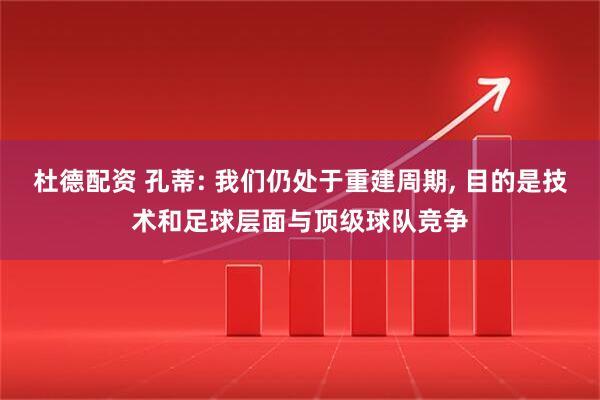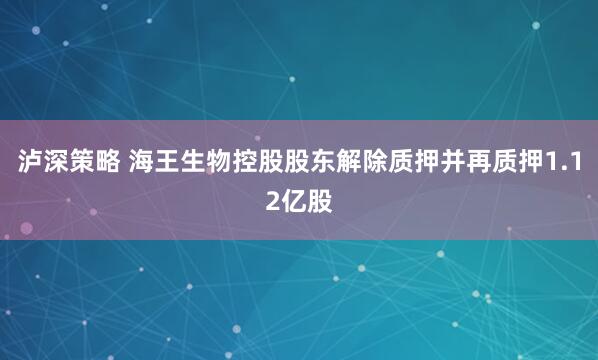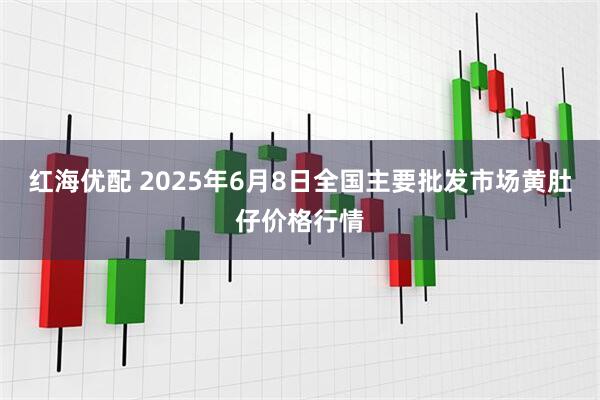今年,网络上掀起热潮的两个流行词——“托举”和“接住”,背后隐藏着一种微妙而略带危险的趋势。人们正试图将“托举”和“接住”这两个原本富有人情味的动作效率化,甚至把它们当作某种绩效指标(KPI)来看待扬帆优配,使得“接住”所代表的情感关系被简化成“提供情绪价值”的冷冰冰交易。
这两个词成为今年不可回避的热词。“托举”在当下不仅仅是简单的动作,它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在大热剧集《苦尽柑来遇见你》中,故事围绕“三代女性的托举”展开,展现了跨代女性间的支持与依靠。在综艺节目《是女儿是妈妈》中,黄圣依的母亲邓传理被誉为“托举式母爱天花板”,彰显了母亲对女儿无微不至的支撑。华大基因CEO尹烨提出的“一代的成功是三代的托举”更是一语道破了家庭代际支持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社交平台上充斥着“托举才是恩典”、“寻找托举自己的文案”等话题,显示出人们对“托举”这一概念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接住”同样火爆。演员周渝民曾谈及大S时说:“我精神不好的时候,熙媛接住了我”,引发无数网友共鸣。电视剧《难哄》中,桑延的一句“不管怎样我都会接住你”更是触动了无数观众的泪腺。类似的“被温柔接住的瞬间”和“我会永远接住你”等句子在网络信息流中频繁出现,成为温情与依靠的代名词。
展开剩余81%不过,热词流行的背后总伴随着反思和质疑。一些人公开表示不喜欢“托举”这个词,认为它过于功利,缺乏真实情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个看似简单的物理动作演变成了抽象的情感支持象征?又为何它们与两年前风靡的“情绪价值”一词紧密相连,成为年轻人心理状态解读的关键词?
“托举”最初是一个具体的身体动作,常见于救援场景中。新闻报道中,“3岁男童悬挂五楼阳台外,3位‘托举哥’紧急救援”、“快递员徒手爬楼托举小孩”等事件中,“托举哥”被视为见义勇为的英雄。除此之外,“托举”也常被用于教育和家庭语境中,如“托举孩子的未来”,将物理动作引申为一种隐喻,象征父母对孩子未来的支撑与期望。
如何理解“托举”的深层含义?
从其物理意义出发,广州日报曾发表评论指出,儿童独自在家频发意外事件,暴露出部分家长的监护失职。文章强调扬帆优配,“看护孩子是做父母最基本的责任”。北京晨报也呼吁:“别总指望托举哥,孩子的安全,父母责无旁贷。”
然而,现实中的矛盾也显而易见。父母需外出工作与照顾孩子之间的冲突,导致“托举哥”频频出现,正反映出许多家庭面临的困境。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现代工业社会基于劳动力商品化,生产与家庭的劳动领域分割形成了彼此对立的结构。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宋少鹏亦认为,社会主义时代职工只需将孩子交由保育机构照看,市场化转型后,育儿等再生产职能被推回家庭,导致家庭承担了更重的责任。由此可见,家庭在子女养育上的“托举”,实则是对社会结构矛盾的回应和反映。
邓传理对黄圣依的支持正是这种“托举”现实的生动写照。从幼年开始,她为黄圣依规划学习路线,安排艺术体育课程,帮助积累资源;即使对女儿婚姻选择不满,也默默为其购置钢琴、冰箱,赠送北京新房。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花十年时间带孙子,让黄圣依得以专注演艺事业。74岁高龄,邓传理还参加综艺节目,为女儿塑造良好公众形象,甚至减重8斤以求上镜效果。在节目中,她坚持爬山,以实际行动表达“我会一直支持你”的坚定承诺。这种精细育儿与密集母职的典范,正体现了现代家庭对孩子未来尽心尽力的“托举”模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曾指出,当前教育问题的根源在于优质资源从公共教育体系中撤出,迫使家庭为市场化教育付出沉重代价,孩子们早早明白“高分是用资源换来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也谈到,尽管改革开放40年催生了大量向上流动的机会,教育作为传统社会阶层上升通道如今却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家长不允许孩子失败或平庸,这种防止社会阶层下滑的焦虑,使得“托举”不仅仅停留在养育阶段,还延伸至婚姻、事业及孙辈教育中。
与“托举”类似,“接住”这一词汇在流行文化中的意义也已超越了字面动作,更多被用来表达情感支持、心理认同与社会互助。心理学家武志红曾指出:“当我们发出声音时,能量被接住并回应,就会转变成明亮的彩色能量;若未得到回应,则能量变为破坏性,表现为不满、愤怒甚至对外界的攻击。”他强调回应与“接住”是爱与力量的根源。
网络上“接住”的温情故事层出不穷。演员周渝民曾坦言自己抑郁时被大S“接住”的经历令人动容。2005年,他因抑郁症在独驾时情绪崩溃发生车祸,大S不顾偷拍镜头,跪地紧抱,成为经典瞬间。然而,类似“接住”的故事也掩盖了更深层的社会问题。周渝民的抑郁不仅是个人基因所致,更与娱乐圈的残酷环境息息相关。他曾直言在圈内“看到太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向上爬的人”,而自己则是“默默做事”的,因而遭受排挤。将其抑郁症单纯归结为大S的“接住”,无形中掩盖了体制性伤害。
电视剧《难哄》中“接住”桥段同样令人感慨。女主温以凡因父亲去世、母亲再婚及性骚扰经历产生心理创伤,梦游不断。她哭诉“无论怎样,你都能接住我”,男主角坚定回应“我都会接住你”。然而,这种温情掩盖了寄养儿童监护失责、社会对未成年保护机制缺失等制度性问题。温以凡和其他受害女孩长期得不到有效帮助,心理问题无人识别,只能自行承受,暴露出公共心理卫生服务的严重不足。
“托举”和“接住”这两个源于身体救援的动作成为热词,恰恰反映出当代年轻人处于一种急需帮助的状态。日本评论家宇野常宽在《〇〇年代的想象力》中提到,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胜利,以《鱿鱼游戏》《饥饿游戏》等“大逃杀”题材为代表的文艺作品反映了年轻人的生存心态:在残酷竞争中互相争斗,为了活下来不得不拼尽全力。然而,即便生活如此冷峻,人们仍渴望温暖,渴求“托举”与“接住”——既需要物质支撑,也渴望情感依靠。
值得警惕的是,当“托举”和“接住”被效率化管理,成为数字化考核指标时,它们所承载的人情味和温度正逐渐消失。例如,邓传理“带孙子十年”“减重8斤”这类数据化描述,将母爱的付出量化;“接住”的情感关系被异化成“情绪价值”的计算公式,情感关系沦为冰冷的利益账本。人类最宝贵的情感体验,正面临被压缩成电子表格中的损益平衡。
此外,个体在激烈竞争中日益孤立,面对变幻莫测的未来,心理和情感负担不断加重,婚恋与组建家庭成为最后的避风港。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重建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尤为重要,既要满足个体对情感支持的渴望,也需推动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实现真正的社会保障和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
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秦萌扬帆优配,编辑程迟,36氪授权发布。
发布于:山东省高忆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