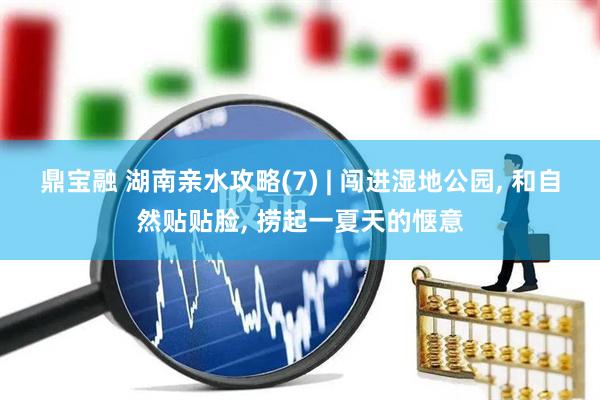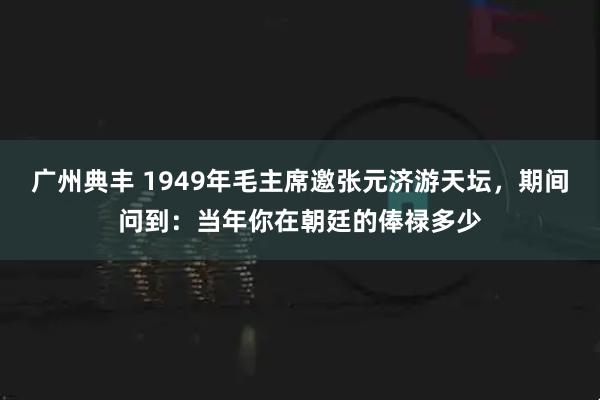
“1949年9月19日下午三点多,天坛祈年殿前传来一句笑问——‘老先生广州典丰,当年在翰林院一个月挣多少?’” 张元济抬头,见提问者正是毛泽东,忙答:“十两白银,再给两担米。”周围随行的程潜、陈明仁、陈毅都笑了。毛泽东又摆摆手:“怕是连今日这壶龙井都付不起吧。”一句闲谈,把新中国领袖与前清进士的距离拉得极近。

毛泽东借半日空闲同几位各界代表到天坛散心,本想简单走走,却被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吸引。张元济曾是光绪二十年的进士,戊戌变法后被慈禧革职,这段履历在场的多数人早已耳熟,可真正与他并肩而行的机会并不多。毛泽东兴致上来,索性边走边聊,从“变法怎么失败”到“出版业的功过”,话题跳得飞快。
若把时间拨回四个多月前,张元济还在上海。5月,陈毅率部进城,白发老人站在旧式宅院门口,看着解放军列队前进,低声说:“这回不一样。”蒋介石电邀他去台湾,他拒了;朋友劝他避一避,他也不动。对他来说,文化不是行李,而是根,根在大陆。
再往前看,张元济的一生几乎被书籍包裹。1898年被革职后,他跑到上海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随后进入商务印书馆。短短几年,“最新教科书”系列铺满全国学堂;《辞源》《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典籍一个接一个问世。同行打趣说:“没张元济,中国的现代课本得晚十年。”他却回一句:“我只是在排字格里找路。”

进入1920年代广州典丰,他把更多精力放到古籍整理。战争连年,古书四散,他主张“化身千百”——多印多留,让典籍在学生手里活起来。他没料到,这套理念后来被新中国的“整理出版古籍规划”直接借鉴。
抗战末期的1948年初,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张元济以院士长者身份致辞,核心只有两字:和平。胡适说他“煞风景”,他却只笑不语。同年冬,国民党局势急转直下,张元济再三被劝离沪,都婉拒。他说:“我不是逃难惯的人。”

上海解放后,陈毅几次登门,表达北平要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想法。毛泽东点名希望张元济出席。老人原本担心记忆衰退,上台说错话,被一句“怀德之士,坐而已”打消顾虑。9月6日,他乘火车抵达北平,下榻六国饭店。一进门就感慨:“我上一次来,是宣统三年的政事堂;房还是这房,天已是新天。”
随后几日,周恩来探访,送来毛泽东的问候。等到19日天坛小聚,毛泽东便抓住机会细问当年往事。谈到戊戌变法,他坦率点评:“关起门改几个章程,不让百姓知道,怎么行?”张元济点头:“那时书生气盛,以为皇上拍板就算数。”毛泽东顺势引到眼前:“所以今日革命,不只靠共产党,还得发动群众,一条船上划桨。”
短暂休息时,毛泽东夸商务印书馆功劳大:“延安那几年,我的书架上常备《辞源》。”陈毅接茬:“这本书救过我们广州典丰,好多生僻字,全靠它。”张元济摆手:“旧学绣花,不值一提。”毛泽东笑道:“新中国同样离不开纸与字,你老人家还得出主意。”

9月21日晚,怀仁堂灯火通明,第一届政协正式开幕。张元济被推为主席团成员,媒体写“83岁无扶杖步履稳”,热度不输青年记者口中的解放军。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望五星红旗升起,扭头对儿子张树年说:“这一刻,比我中进士还痛快。”
1950年初,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命张元济为委员。一个半月后,老人突发脑血栓,左侧瘫痪。陈毅派专车送医,毛泽东回信宽慰:“身体要紧,其他事慢慢来。”病榻之上,张元济仍惦记文化事业。他连续给中央写信,为西藏办学与藏文出版提建议,部分被采纳。

1953年,上海筹建文史研究馆,中央点名张元济任首任馆长。老人起初顾虑自己行动不便,陈毅再赴寓所,说出毛泽东的原话:“上海文史馆,没有比张先生更合适的。”他这才同意,就任后常拄杖巡视书库,“看看这些字排得正不正”。
1955年,他写信给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劝其以民族大义为重。“钱鏐能归宋,何况今日?”毛泽东得知后,在一次干部会上点名表扬:“学问人也能立大义。”
1957年冬,张元济病重住院。周恩来专程探视,轻声报自己姓名。老人微睁眼睛,第一句话仍是:“毛主席可好?”听到“很好”,他露出微笑。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辞世,遗诗一句“泉台仍盼好音传”,写尽未了之愿。治丧委员会名单里,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分列致哀首席。

从科举出身到新政协元老,张元济走了九十二年,跨了三个时代。毛泽东那句“得靠群众”与张元济那句“化身千百”其实并不矛盾:一边是政治动员,一边是文化普及。两种力量在1949年的天坛交汇,留下了“十两银子”的玩笑,也见证了古老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跃迁。
高忆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