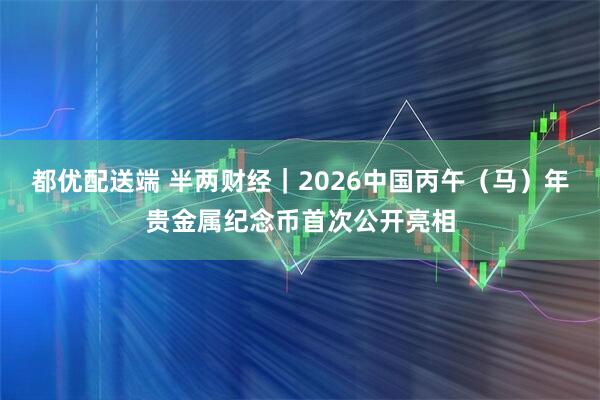吕文扬和段元这天到元诚小学后墙这边画画凯丰资本。
墙边的爬山虎正疯长,段元坐在掉漆的蓝色铁艺秋千上,调色盘里的钴蓝和赭石混成了一滩泥浆色。他盯着画板上歪斜的钟楼尖顶,笔尖悬在空中迟迟未落——第三张水彩纸了,晾在旁边的两张都被风吹到了蒲公英丛里。
吕文扬的速写本沙沙作响。他坐在双杠上,小腿晃动的节奏惊飞了围栏上的麻雀。段元偷瞥他的画纸,却看见满页都是自己皱眉的样子,连额角那道小时候爬树留下的月牙疤都分毫不差。"画风景,吕大摄影师。"段元把洗笔筒的水甩过去,水珠在阳光里划出虹弧,落在吕文扬的帆布鞋上,洇出深色的斑点。
正午的太阳烤化了柏油路上的白漆。段元忽然丢下画笔,从书包里掏出罐装可乐,冰凉的铝罐贴上吕文扬的后颈。他们同时听见"咔"的轻响——吕文扬的铅笔芯断了,在画纸角落戳出个小小的黑洞,像突然闯入的日全食。
颜料在高温下干得很快。段元新调的青绿色已经结膜,他蘸水化开时,笔杆上的"Y.W.2023"字样在光下一闪——这是去年写生集训吕文扬刻的,当时他们共用一盒颜料,所有的笔都缠着不同颜色的胶带。
展开剩余37%钟楼敲响三点时,一群穿背带裤的小学生呼啦啦涌进操场。有个扎羊角辫的女孩蹲下来看段元的画:"哥哥,钟楼为什么是粉色的?"段元愣住,这才发现调色盘不知何时被吕文扬混进了玫瑰红。而此刻那人正靠在单杠边,用炭笔在速写本背面飞快涂抹——画的是段元发红的耳尖,和沾满水彩的左手,小指上还挂着半片干涸的鸢尾花瓣。
蝉鸣突然沸腾的刹那,段元抓起最艳丽的朱红色,在吕文扬画本的留白处摁了个指印。像夏天突然长出的一颗莓果,又像某种无需语言的印章,在下午三点二十七分的阳光里凯丰资本,缓慢地风干成永恒的形状。
发布于:安徽省高忆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相关文章
沪深京指数
热点资讯